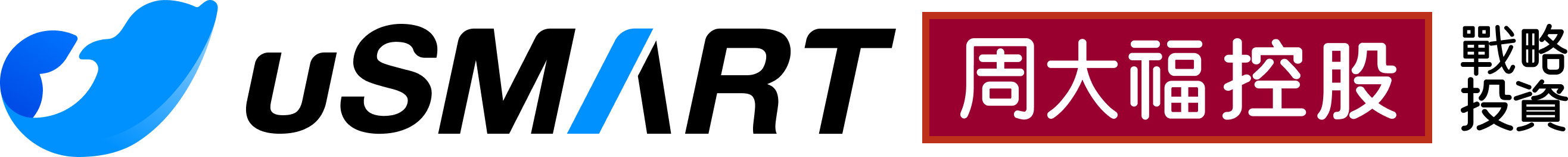作者:清和 智本社社長
來源:智本社
當下ChatGPT正在掀起一股內容生成式人工智能革命浪潮。ChatGPT作爲一項有力的競爭工具,誰先引入ChatGPT,誰便獲得競爭優勢,正如近水樓臺先得月的微軟。對普通大衆尤其是知識工作者來說,ChatGPT最直接的挑戰可能是丟掉工作。
據美國《財富》雜誌網站報道,一家提供就業服務的平臺對1000家企業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近50%的企業表示,已經在使用ChatGPT;而已使用ChatGPT的企業中,48%讓其代替員工工作。
ChatGPT引發了廣泛的失業焦慮,人工智能革命真的會發引發技術性失業嗎?本文(撰寫於2019年)從經濟學的角度專門探討技術進步與就業(失業)的關係;同時,清和社長推薦音頻課程《技術性失業》,讓我們更深層次地理解技術創新如何作用於經濟系統。
2019年世界人工智能大會上,馬雲與馬斯克上演了一出雞同鴨講式的“雙馬尬聊”:
馬雲:“過去100年我們一直擔心新技術將會帶走就業機會,但實際上我們創造了很多就業機會。”
馬雲對人工智能持樂觀態度,不擔心機器替代我們的工作崗位。
馬雲接着說:“計算機就是機器,機器就是一個玩具。我們要有信心,機器只有芯片,而我們有心,我們的心是智慧的來源。”
“因爲人是不一樣的,機器是人類發明的。根據科學,人從來無法創造一個比自己更聰明的動物,在這里有很多聰明人,但我們還是沒有辦法創造一個更聰明的人。”
到這里,馬斯克忍不了了,來了一句:“我非常不同意你的看法。”
馬斯克:“像你說的,聰明人犯的最嚴重的錯誤就是自以爲聰明。”
馬斯克例舉了阿爾法狗下棋的例子說明,“計算機已經在很多方面比人更聰明瞭”。
馬雲腦瓜子靈活,話鋒一轉:
“和計算機下棋這很愚蠢,像100年前人們創造了機器,人們說我可以比汽車跑得快這是不可能的,只有傻子纔會去和汽車賽跑……我們要做我們擅長的事情。”
又一頓尬聊之後,馬斯克說了一句:“AI本來就是愛。”
有人說,這是一段科學與玄學的對話。
馬斯克,經濟學及理工科出身,幹得都是飛天遁地、殖民火星的冒險之事。
素有“鋼鐵俠”之稱的他,對話具有前瞻性、科技感以及悲觀色彩,對人工智能保有敬畏之心,呼籲多學習、多思考,以探索宇宙的無盡與未知。
馬雲,英語老師出身,數學成績不理想,但思維敏捷、心大膽肥以及觀念前沿。
對技術不瞭解的他,在對話中試圖削減技術含量,拉回到他擅長的軌道上來,對人工智能保有樂觀態度,且富含“馬氏”邏輯。
如此,備受期待“雙馬會”淪爲令人大跌眼鏡的雙馬尬聊。
馬雲與馬斯克,代表了兩種完全對立的主張,反應了東西方之間、文理科之間、樂觀派與悲觀派的思維差異。
馬斯克的理性悲觀,透露出對科技、宇宙及未知的敬畏,沒有明確的結論,強調多學習、多思考、多創造。
馬雲的感性樂觀,體現了對人類智慧保持自信的理想主義,以歷史經驗和社會學的邏輯給未來下明確的結論。
對於普通人而言,雙馬尬聊的焦點是:我們的工作,是否會被人工智能替代。
技術進步是否會造成技術性失業,這是一個爭論已久的老話題。
關於技術性失業的擔憂古已有之。
早在公元初年,古羅馬韋帕薌皇帝時期,有一次爲運送一根石柱到正在修建中的神廟,需要動用大量勞力。這時,有一位發明家求見皇帝,建議他用自己新發明的機器運輸石柱。
儘管這個新機器可以大幅減少運輸石柱的成本,但皇帝還是拒絕了發明家的建議,理由很簡單:如果採用了機器運輸,那麼那些搬運石柱的民工將會因此丟掉飯碗。
後來,這個話題,出現在美國總統大選上。
華裔楊安澤宣佈競選總統,蹭着特朗普的熱度,與之爭鋒相對。於是,與楊安澤攀親戚的人就多了起來。
在2016年大選中,特朗普瞄準製造工人失業議題逆襲希拉里。這次,楊安澤緊跟特朗普打出“機器人將至”的競選議題。
特朗普說:中國人搶走了美國製造工人的工作崗位。
楊安澤說:特朗普看對了失業問題,但是找錯了理由,開錯了藥方。
在楊安澤看來,80%的失業是自動化造成的,只有20%是工廠轉移國外所致。
楊安澤嘲笑政客:在你們玩身份政治的時候,我們的工作已經被機器人搶走了。
美國工人的工作,到底是被機器搶走了,還是被中國人搶走了,這已成爲了政治博弈、博取選票的議題。
從上帝視角來看,技術性失業顯然是杞人憂天。但從短期來看,人工智能替代我們,是一種日益迫近的焦慮。
如何避免盲目樂觀或焦慮不安,理性認知技術性失業?
技術與經濟之間的關係,是一條非常關鍵的線索。
本文邏輯:
樂天派:爲何不用勺子挖地?
悲觀派:誰能預測技術創新?
折衷派:技術性失業存在嗎?
1
樂天派
爲何不用勺子挖地?
上個世紀90年代,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在亞洲考察時偶然來到一個工地。
弗里德曼發現工人們在用鏟子挖運河而沒有使用重型機械,他感到很奇怪,便詢問了當地的官員。官員回答說:“用鏟子是爲了創造更多的就業。”
“噢,原來是就業計劃,我還以爲你們是在修運河呢。” 弗里德曼說道,“既然是想創造就業,那別用鏟子了,用勺子挖吧。”
弗里德曼屬於技術性失業的樂天派。弗里德曼是新自由主義的領軍人物,他相信,市場充分競爭的力量,對市場補償機制解決技術性失業充滿信心。
早在18世紀,英國工人盧德帶領工人搗毀工廠機器,他們抱怨機器奪走了他們的工作。
與盧德生活在同一個國家、同一個年代的古典主義經濟學家們,如薩伊、馬爾薩斯、李嘉圖,都對“盧德運動”嗤之以鼻。
古典主義經濟學家都否定技術性失業的存在。
薩伊堅持“供給創造需求”,認爲採用新機器所導致的產品供給增加會引起產品需求的增加,產品需求的增加最終會引起勞動力需求的增加,從而使得被新機器排擠的工人重新獲得就業機會。
馬爾薩斯則認爲機器的應用會通過需求不足、資本短缺等因素引起失業,但他同時又指出,開放的市場可以恢復充分就業。
李嘉圖起初也相信市場的力量可以補償機器對就業的排擠,但後來“由於他特有的科學的公正態度和熱愛真理,斷然收回了這種觀點”。
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第三版中特意增加《論機器》一章,認爲如果機器佔用了流動資本,則會出現嚴重的就業問題。
古典主義的觀點,跟今天我們很多人的觀點類似,即技術進步導致一部分人失業,同時也創造了新的就業機會,這就是市場的補償機制在起作用。
市場到底是如何補償的呢?古典主義總結了五種補償機制:
一、新機器補償機制:技術進步產生的新機器替代舊機器,新機器所締造的工作崗位補償了被技術進步排擠的就業。
例如,數控車牀替代傳統車牀,數控車牀的設計、製造和使用都需要新的技術工人和工程師。
二、價格下降補償機制:技術進步可以降低商品成本,進而讓需求增加,產出和就業擴大,實現補償。
這是一種典型的古典主義範式。
例如,互聯網降低了購物的交易費用,網購價格更便宜,用戶會忍不住的“買買買”,天貓“雙十一”的銷量已經超過了2000億,社會需求擴大了,就業也就增加了。
難怪馬雲如此樂觀。
三、新投資補償機制:新技術促使成本下降,但是售價有可能沒有同比例的下降,這樣廠商就有了額外的利潤,工廠老闆就有意願增加投資,創造新的就業。
古典主義提出的新投資補償機制,實際上間接承認了價格機制的滯後性,或凱恩斯主張的價格黏性。
例如,無人售貨機和24小時銀行可以降低開設網點的成本,但是商家和銀行一般不會降價,而是乘這個機會窗口投資更多的無人售貨機和自助櫃員機。
四、新產品補償機制:技術進步帶來的新產品將創造新的生產部門和就業崗位。
例如,無人機的出現,創造了一個新的產業和大量的工作崗位。
五、工資下降補償機制:技術創新引發失業,失業人口多了,勞動供給增加,勞動力的價格就會下降。這個時候,一些廠商就會增加對廉價勞動力的僱傭,或開發勞動密集型技術,以降低成本。
例如,農業機械化過程中,農村大量勞動力剩餘,並遷移至城市成爲廉價勞動力,外資增加製造工廠投資,吸收農民工,對農民失業構成補償。
工資下降補償機制後來還成了新古典經濟學家解決一切失業問題的處方。
以上五種補償機制是古典主義派經濟學家們的理論主張,他們的後來者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們不但繼承完善了這些補償機制,還提出了一些新的補償機制。
以馬歇爾、瓦爾拉斯、帕累託爲代表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他們引入了邊際理論和數學實證方法,其理論主張比古典主義邏輯更嚴密、論證更精細。
新古典主義提出了商品價格“彈性”的概念,應用在價格下降補償機制中是這樣解釋的:
有些商品價格彈性大,比如大閘蟹,如果打五折很可能會引發搶購,生產和就業會擴大。但有些商品彈性小,比如食鹽,即使買一送一,很多人也無動於衷,並不會增加購買數量,這就難以起到補償作用了。
庇古引入了貨幣機制,他認爲,價格下降意味着實際貨幣供給增加,利率因而下降,這將產生投資激勵的作用,從而增加產出和就業,這就是庇古效應。
現實中,是否會發生庇古效應呢?
過去一個世紀里,汽車的技術一直在進步,但價格卻在下跌,汽車是耐用品,彈性比較低,個人一般不會因汽車降價而多買兩臺車。
但是,汽車降價卻會讓個人的錢變得富餘,有些人會將多餘的錢存入銀行或做投資,而有些人會增加旅遊等消費,從而促進生產和就業。
工業部門技術進步快、生產效率高,工業部門的貨幣溢出到了服務部門,擴大了服務部門的需求和就業。這就是發達國家商品便宜、服務貴的重要願意。
對於新產品補償機制,新古典主義則進一步考察了新舊產品之間的可替代性就業補償程度的影響,通過對比結論仍然是樂觀的。
例如,智能手機替代功能型手機,市場需求、投資以及就業都大幅度提升。
在古典主義提出的五種補償機制外,新古典主義還增加了收入增加的補償機制和新投資激勵補償機制。
六、收入增加的補償機制:由於技術進步帶來成本下降的好處被工人和僱主分享,工資和利潤都得到提高,產生收入效應。如此,消費和投資都會增加,同樣就業也會增加。
七、新投資激勵補償機制:技術進步會導致投資邊際效率提高,利潤預期上升,這種情形下老闆們一般會追加投資,就業也隨之增加,這一機制被稱爲 “熊彼特效應”。
所以,早期的經濟學家基本都是樂天派,他們認爲,沒有任何外在因素可以衝擊市場的自然循環,技術帶來的短暫性失業也會被市場的補償機制所燙平。
2
悲觀派
誰能預測技術創新?
經濟學誕生後150年間,過度推崇市場理論及均衡範式的經濟學家們,對技術性失業視而不見,儘管這一經濟危機和大規模失業不斷降臨。
但是,20世紀前30年發生了兩件事情,改變了經濟學家對技術性失業的看法。
第一件事情是美國1919—1925年間生產率數據的第一次公開出版。
這一數據表明,這個時期美國生產率(即每個工人的平均產出)提高了59%,而與此同時就業率大幅度下降。
面對這一反常現象,經濟學家推測技術性失業的存在。
第二件事情就是1930年代的大蕭條——真正讓經濟學界重視失業問題並引發第一次大爭論。
其實,早在20世紀初,凱恩斯就象徵性地提到了“技術性失業”,他指出“我們正在爲一種新的疾病所苦惱。”
大蕭條到來,經濟崩潰,失業大增,這意味着市場的失靈,市場補償機制不起作用。當時,整個經濟學界都傻眼了,凱恩斯以有效需求不足理論推翻了新古典主義。
補償機制失效,經濟學家自信樂觀的理論根基被大蕭條踢爆了屁股。
這兩個事件促成了當時經濟學界流行的觀點,即肯定了技術性失業的存在。有人甚至提出暫停技術進步的建議,美國參議院和衆議院甚至分別在1939年提出了對機器徵稅的議案。
大蕭條之後,人們認識到,對待失業或技術性失業不可盲目樂觀,市場也有靠不住的時候。
爲什麼市場補償機制會崩潰(市場失靈)呢?
在經濟現實中,價格彈性程度、貨幣制度、財政制度、勞動制度、壟斷性質、金融市場的脆弱性等,都有可能阻礙價格與供給機制的充分發揮,從而阻斷或減少失業工人再吸收,破壞市場均衡,造成技術性失業。
費雪用“債務螺旋”理論來解釋。凱恩斯用以三大心理規律爲基礎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論來解釋。熊彼特則用破壞式創造來解釋。
熊彼特的解釋令人信服,爲什麼?
以上古典主義和新古典主義的七大補償機制,都有一個前提——技術水平保持不變。而熊彼特,瓦解了這個前提。
熊彼特認爲,技術創新是造成非均衡的主要因素,市場在破壞式創造中動態演進。
例如,爲什麼大量傳統的木匠、鐵匠快速消失了?
機器生產木製傢俱和鐵製品,成本更低、質量更好,機器的大規模生產及成本質量優勢,對傳統木匠、鐵匠的替代速度極快,市場還來不及反應,這些匠工就失業了。
這就是技術創新對市場均衡及充分就業的衝擊,即熊彼特的破壞式創造。
熊彼特指出,創造性破壞是經濟低谷時企業家以創新求生存,成功的技術創新進而促使經濟復甦,如此循環反覆構成動態均衡。
每一次的蕭條都包括着一次技術革新的可能,或者說技術革新的結果便是可預期的下一次蕭條。
熊彼特贊成技術衝擊的主張,認爲技術革命帶來的失衡、危機和失業不可避免。
19世紀英國紡織業發生多次過剩性經濟危機,正是受到蒸汽機的技術正向衝擊。
這一時期由於蒸汽紡紗機的廣泛應用,一名工人將1磅棉花紡成紗線所需時間由過去的500小時縮減到只有3小時。紡紗機和織布機的引進節約了大量勞動力,這使得工人們擔心出現失業,進而引發“盧德運動”。
所以,從大蕭條開始,人們逐漸從非均衡的角度研究技術與經濟之間的關係。
這種主張,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創新理論領域誕生了兩種對立的理論:需求引致創新理論和自發創新理論。
需求引致創新理論,屬於古典主義樂觀派,否定技術性失業。這種理論認爲,經濟可以掌控技術,技術進步完全服務於經濟,是對市場條件被動、機械的反應。
自發創新理論,則屬於技術主義悲觀派,支持技術性失業。這種理論認爲,技術的演變受自然科學規律支配,而非經濟學規律。
技術有自己的自然科學規律,不以人的喜好爲轉移,不是想實現就能實現的。
比如,以前人們想着在自己身上安裝一對翅膀就能飛起來,後來屢屢失敗。
又比如,科學家開始認爲機器人能夠像人類一樣思考。後來發現錯了,機器人無法像人類的電腦一樣思考,但可通過算法來完成。
技術的不確定性以及擴散性,造成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容易衝擊市場均衡,造成技術性失業。
技術進步遵循自然科學規律,技術演進像浪潮,前期積累大量能量然後突然爆發達到高潮,而經濟無法決定技術積累到什麼程度爆發,難以預測浪潮的頂點在何處。
任何技術開發存在風險,很多時候最前沿的技術員也不知道何時能夠成功,甚至是否能夠成功。
技術創新,尤其是技術革命,會帶來巨大的衝擊波,技術外溢還會帶來很多餘波。這些都是技術的不確定性帶來的。
經濟學家、企業家、科學家都難以全面預測技術帶來的各種衝擊。技術的衝擊,往往是突發性的、突變性的和不穩定性的。
從1788年到1825年,一共37年間,英國發生了7次經濟危機,幾乎都是過剩性經濟危機,危機的嚴重性和波及程度一次比一次大。
這個階段,瓦特發明的蒸汽機大規模使用到棉紡織領域,生產效率立即大幅度提升。
當時,英國一年的棉紡織品的產量,相當於過去幾個世紀。英國人、歐洲人徹底告別了嚴寒。
別小看一張被子、一件棉襖帶來的變化,這一變化直接改變了歐美世紀的社會關係。
人們告別了嚴寒,因風寒而引發的疾病大幅度下降,人口自然死亡率下降,人口出生率提高。1840年之前,英國人口大量出生,並往城市集中。
這給當時的英國社會經濟帶來巨大的衝擊。
首先,大量的人口紅利出現,促使工業生產飛速發展。
其次,大規模人口集中到城市,促進了城市化進程,英國倫敦成爲全球第一大城市。
最後,大量人口出生及集中,城市公共用品嚴重不足,這導致英國、歐美的社會矛盾極爲尖銳,工人運動不斷。
後來,法西斯上臺以及蘇聯建立,對世界造成了巨大改變。
這就是蒸汽機和電氣技術浪潮給英國棉紡織業帶來不可預知的巨大沖擊。
這些衝擊根本上都是技術變革帶來的。但是企業家、政治家都無法預測技術變革、技術擴散帶來的衝擊,因而引發了一系列的社會經濟問題。
再拿頁巖氣爲例,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全球原油價格漲到歷史高位。
當時中國做出的戰略選擇是發展新能源,大力扶植電力作爲替代能源。
美國這個時候頁巖氣取得了技術突破,頁巖氣產量大幅度提升,美國從原來的原油進口國搖身一變成原油出口國。
這就是頁巖氣革命。
美國減小了對中東石油的依賴,也轉變了對中東的戰略,將重心重回亞太。
受頁巖氣革命影響,全球原油價格大幅度下跌,一些產油國尤其是俄羅斯壓力非常大。俄羅斯因石油出口創匯不足,在美元加息週期中引發了貨幣危機。
這就是技術積累的不確定性給經濟帶來難以預估的衝擊。
我們再來看看電力技術。其實早在100多年前,電池動力和內燃機動力差不多同時起步。電動車的發明甚至要早於內燃機車。
1900年時,蒸汽車比重最多,其次就是電動車,然後纔是油氣燃料車。所以,我們說電力是新能源,其實不符合歷史。
但是,後來市場一邊導向內燃機動力。主要原因是汽油、柴油的壓縮密度和燃燒效率遠遠高於電池動力。
實際上,這100多年來,人類花了很多時間和資金投入電池技術的研發,但是進步極其微小。
從另外一個角度,我們也不知道,電池技術何時突破。全球花了很多經費在鋰電池上,但效果不盡人意。
日本在福島核電站泄露事件後,能源戰略開始去核化,轉向氫燃料。如今,日本的氫能源及氫燃料汽車技術先進,但是距離大規模量產依然有距離。
與日本不同,美國特斯拉則走純電動車路線,中國在氫燃料上投入不多。
不管是氫燃料,還是鋰電池,我們還不完全確定電池技術何時突破,在哪個方向上突破。
假如電池技術哪天突然被突破,或許對很多高耗能行業形成替代性,如內燃機汽車。這樣或許會突然造成石油開採、銷售以及內燃機制造等相關領域的大規模失業。
由於知識和科技有外部性,經濟系統無法阻止、也無法決定技術的廣泛外溢、延伸以及大規模推廣應用。這就導致其他產業有可能突然出現結構性失業。
另外,新技術一旦成熟,其普及、擴散及替代勞動力的時間越來越短。美國曾經花了80年才使汽車的普及率達到50%,但電視機和錄像機達到這一程度只花了30年,手機則僅僅用了10年。
在人工智能方面,我們同樣面臨這種不確定性的衝擊。如果工業機器人一旦實現量產型突破,那麼全球很多工人都可能突然被機器人所替代。這種短時間引發的大規模技術性失業對經濟的衝擊很大。
技術積累的不確定性,本質上是人類對自身智慧上限的不明確。
科學家無法保證何時能夠攻克阿爾茨海默病,無法確定奇點臨近的具體時間。
我們無法預測基因技術的進步,會對哪些行業、領域以及家庭帶來什麼樣的衝擊。
有些技術看似變化微小,看似隔行如隔山,但是技術的擴散性極強,很可能對其它行業造成顛覆。
馬化騰還曾在知乎上發佈提問:“整個人類處於互聯網發展的哪個階段?下一個十年,互聯網升級的大致方向在哪里?”
馬斯克對人工智能、未知宇宙表示過擔憂、謙虛與敬畏。
技術演進遵循自然科學規律。在自然、宇宙及規律面前,人類依然很渺小和無知。
所以,對技術的不確定性、技術性失業及人工智能,我們應該有更多的敬畏。
3
折衷派
技術性失業存在嗎?
熊彼特吸收了奧地利學派和新古典主義兩大流派的思想,抓住技術進步(企業家創新)這一個點,破解市場均衡。
實際上,熊彼特是第一個全面論述技術與經濟關係的經濟學家。他採用折中主義的思想論述二者之間的關係。
一方面,熊彼特認爲,技術進步是經濟發展的中心,技術創新是造成非均衡的主要因素。
他具體理由是:
第一,創新不是均勻地隨機分佈於整個經濟中,而是集中於某一些關鍵部門,這將引起不同部門間的結構調整問題。
他把技術進步同經濟週期聯繫在一起,認爲大規模失業與創新活動在歷史上是一致的。
第二,創新的擴散過程也是不均勻的,具有週期性。
第三,創新發生後的迅速增長期間,利潤預期發生變化,增長在達到一定程度後會因利潤預期的變化而減慢下來。
另一方面,熊彼特並不認爲,經濟系統會被技術創新“肆意”破壞——人們常常陷於不確定的失業危機之中。
他主張,創新不是一個技術概念,而是一個經濟概念:它嚴格區別於技術發明,而是把現成的技術革新引入經濟組織,形成新的經濟能力。
熊彼特認爲,“當技術因素與經濟因素相沖突時,讓步的一定是技術因素。但是我們並不能否定它的獨立存在和意義,以及工程師觀點的健全性。因爲,雖然經濟目的支配着實際使用的技術方法,但弄清楚方法的內在邏輯而不考慮實際障礙還是有意義的。”
熊彼特的折中主義,更加側重於經濟決定技術論。
到1982年,意大利經濟學家喬瓦尼·多西同樣奉行折中主義,綜合了需求引致創新理論和自發創新理論,完整地論述了經濟與技術之間關係。這就是“技術範式-技術軌跡”理論。
多西認爲,技術決定論和經濟決定論都有偏頗,自然規律與經濟規律互爲獨立,但二者相互影響。
技術範式負責爲技術發展指出一組可能性的方向,這組可能都是由自然科學規律決定的。
至於走哪一條路,由經濟規律決定,也就是由市場來選擇,確定什麼樣的技術路線最具有商業化的可能性——成本更低、效益更高。
舉個例子,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信息技術剛剛起步之時,關於數據庫技術範式,其實有多種選擇,比如中心化數據庫和分佈式數據庫,最終選擇哪一種呢?
後來市場選擇了更加安全、穩定、高效的中心化數據。這就形成了今天我們熟悉的技術軌跡,如谷歌、微信、阿里巴巴的中心化數據庫控制着所有用戶的數據。
2008年,中本聰發佈了《比特幣——一種點對點的電子現金系統》白皮書,標誌着一種新的技術範式進入市場,那就是分佈式計算。分佈式計算結合了密碼學中的非對稱加密技術,形成無人可篡改的賬本,這就是區塊鏈。
分佈式和集中式,都遵循自然科學規律,但什麼時候用哪種技術,取決於經濟規律——成本、收益、風險考量。
所以,科學家、機器人或資本、企業家都不可能單獨掌控這個世界,經濟的脈象由自然規律和經濟規律共同支配,技術性失業與否取決於這兩大規律的配合度。
將自然規律與經濟規律相結合思考技術性失業:
一是技術成熟度與規模經濟。
能否形成規模經濟,是開發、引進、推廣技術的關鍵考量。一項技術能否快速並大規模應用,並不是完全取決於技術的成熟度,而是能否解決實際問題並帶來規模經濟,或者與其他資源如勞動力相比,是否具有替代優勢。
我舉個例子,爲什麼美國農莊里的大型機械,沒有在日本、中國、泰國等人口稠密的亞洲國家大規模應用?
原因是,亞洲國家最大的資源優勢是勞動力,而稀缺的是土地。這就決定了這些國家的農業經濟在選擇技術上,不是替代勞動力的大型機械,而是解決土地稀缺問題的高效生物技術。
反過來說,農業機械在亞洲梯田上不會產生規模經濟,而農藥、化肥及育種技術可以形成規模經濟。
所以,中國纔會出現袁隆平雜交水稻。日本則選擇先化學化、後機械化現代農業發展道路。日本是世界上最早實現農業化學化的國家,搞精耕化農業種植及管理。美國的農業機械技術,並未造成東亞農民失業。
人工智能也是這個道理。日本、美國的汽車製造都是資本密集型,如今的特斯拉是技術密集型,美國特斯拉工廠採用全智能化流水線生產。
但是,特斯拉也在中國設廠,也考慮中國廉價的勞動力及土地資源,而不是直接將智能流水線轉移到中國。在中國的勞動力與美國的智能化之間,馬斯克經過了成本與收益的考量。
再如,美國亞馬遜嘗試用無人機解決“最後一公里”問題,中國順豐在城市基本都在使用廉價勞動力“跑腿”配送。
1913年,福特汽車建造了世界上第一條流水線,當時流水線上還有不少工人作業。100之後的今年,福特汽車公司整車自動化裝配生產線上都是激光焊接機器人在作業。
從第一條流水線到全自動化機器人,福特公司經歷了一百年的技術積累及逐步替代。
在美國,最新的自動化圖像處理軟件能完成放射科醫生的大部分工作,成本連原來的 1% 都不到;但是人工智能敲開門診部、手術室的大門還有非常遠的距離。
曾經有媒體報道,有些人工智能公司僱傭工人替代機器人。美國一家創業公司總裁格里高利曾開玩笑說:如何創辦一家AI公司?第一,僱一羣低薪者假扮AI;第二,等待AI被開發出來。
所以,技術性失業,實際上是技術進步在替代該替代的、沒有競爭力的勞動力。如果廉價勞動力具有優勢,不但不會被技術所替代。市場會根據技術的成熟度、成本、效益,逐漸淘汰該替代的勞動崗位。
二是技術創新是經濟系統協同的結果。
我們最容易犯得錯誤是,設想突然出現無數成熟的機器人,在流水線裝配,在送快遞,在開車,在翻譯,在做美食……然後,人類什麼都不能做,徹底失業了。
現實並非如此,一項重要的技術革命,一定是在自然科學規律上經歷了大量的累積。這累積過程不但需要時間,還要各技術領域同步突破、相互配合。
舉個例子,智能手機在2007年iPhone身上爆發,並非來自蘋果一家的創新,而是整個電子產業——芯片、鏡頭、通信、屏幕、存儲、內存、電池、工業設計,以及軟件產業如系統,安全、人工智能、應用市場、雲服務,還有製造業如自動化裝配、精密製造,共同積累到一定技術水平上的結果。
又如我們最擔心的人工智能。一個成熟的機器人,最基本的需要是具備人機交互及識別、環境感知、運動控制三項核心技術;依託這三大技術,配套電池模組、電源模組、主機、存儲器、專用芯片等基礎硬件以及操作系統。
由硬件和操作系統構成機器人整機,整合基礎硬件、系統、算法、控制元件,形成滿足一定行走能力和交互能力的機器人整機;在此基礎上形成各種基礎應用開發,基於機器人操作系統開發的控制類APP、管理員APP和各類應用程序App等;產生的數據將有羣組服務、雲服務、大數據服務等。
每一種應用性機器人如無人駕駛、工業機器人、智能醫療設備,還要配合汽車製造、工業設計、醫療技術等進步。
三是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互爲促進。
1954年,產業工會聯合會主席、勞工運動領袖沃爾特·魯瑟來到克利夫蘭,參觀福特公司的一座工廠。
一位經理驕傲地向魯瑟展示了福特公司先進的自動化機器,他對魯瑟說:“你打算怎麼向這些機器徵收工會費呢?”
魯瑟的迴應是:“你又打算怎麼讓它們賣汽車呢?”
魯瑟的意思是,如果工人都失業了,機器生產出來汽車及商品都沒有人購買。
如果技術積累到一定程度出現規模經濟,對大規模的勞動力形成一次性、全方位替代,那麼,大規模的技術性失業不利於消費增長,反過來對技術應用、創新及經濟進步構成牽制。這種微觀反制在宏觀上並不完成成立。
正確的理解是,技術造成結構性失業的同時,創造了新的有效需求。
對我們個人來說,避免被技術打敗的最好辦法是,正如馬雲所說的,不要和汽車比賽跑。
後記
卡辛斯基的忠告
出於對自然規律和人性的敬畏,“狂人”卡辛斯基的忠告依然值得我們警惕:
“工業化時代的人類,如果不是直接被高智能化的機器控制,就是被機器背後的少數精英所控制。”
其實,真正要擔心的不是人工智能,而是掌控人工智能的精英——數據確權是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