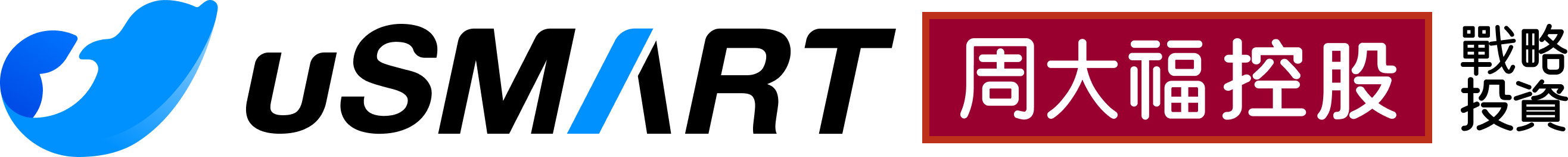作者:老喻
來源:孤獨大腦
一個理性的人會捍衛自己的觀點,但也不拒絕在相反的方向下注,以實現對衝。
給人一條魚,你可以養活他一天;
教會他如何套利,你就能養活他一輩子。
——華爾街的老話
開始
2022年最賺錢的對衝基金,是肯·格裏芬的城堡投資。其業績極其閃亮:
1、爲客戶淨賺160億美元;
2、公司賺了近120億美元的管理費和業績分成;
3、其中旗艦基金收益率達到38.1%。
每年“賭場”都有大贏家,很多是靠運氣,即使是那些所謂的天才。
例如,此前賺錢最多的記錄,是由“華爾街空神”約翰·保爾森在2007年經典的“大空頭”一役中創造的156億美元紀錄。
封神之後,保爾森做多黃金,再次大賺50億美金。
而從2011年開始,“大神”開始失去神奇,旗下基金連續虧損,管理資金從380億美元大幅縮水至數十億美元。
這讓我想起《巴斯特·斯克魯格斯的歌謠》裏的西部片真理:
自命不凡的快槍手,死於更快的槍下。
相比而言,肯·格裏芬似乎有點兒不一樣。
1
作爲一名建築供應商的孩子,格裏芬從小“對世間萬物如何運轉好奇不已”,並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高中時期學習了計算機編程。
在哈佛讀書時,格裏芬開始鑽研可轉換債券套利。爲了找尋被錯誤定價的債券,他自己編寫了軟件,還在宿舍樓頂架設了衛星天線。
格裏芬的策略是:買入價格過低的權證並用賣空相應股票的方式對衝。
這正是愛德華·索普的“德爾塔對衝策略”。
聰明人總是試圖通過自己的超凡智力來“變現”。
1960年前後,在麻省理工學院教書時,索普發現了玩兒21點遊戲有機會獲得微小的戰勝賭場的概率優勢。
如此一來,原本站在賭場那一邊的大數定律,開始服務於“概率黑客”。
僅有這一點還不夠。
由於賭場有“無限”的籌碼,即使索普擁有了細微的概率優勢,也可能被擊垮。
信息論創始人香農參與了這次戰勝賭場的智力挑戰。他引導索普藉助凱利公式決定下注比例,從而解決了以有限籌碼對抗無限籌碼的難題。
於是,那微弱而隱蔽的概率優勢,變成了可以複製的賺錢祕訣。
事實上,香農自己在股票投資上的回報也非常高。
索普的探索開啓了天才們的財富徵途:
馴服隨機性,與財神對賭。
從賭場到金融市場,索普繼續在隨機性的世界裏探尋財富的密碼。
他發現,股票權證的定價往往偏高,所以做空權證似乎是賺錢的好機會。
當然,作爲一位下過賭場的數學家,索普絕不會只靠一個水晶球就出手:
即使權證定價偏高,但如果被高估的股票繼續上漲呢?
這類事情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裏再常見不過了。
難題之一:一個骰子的隨機性,可以被概率描述,可以被大數定律“顯形”;
難題之二:人類慾望和行爲的“不確定性”,則有索羅斯所言“反身性”的那類無法預測的癲狂。
索普的策略是“套利”:
一邊賣空定價過高的權證;
一邊買入股票作爲對衝。
這樣的話,不管是定價過高的權證下跌,還是被高估的股票繼續上漲,下注者都可以兩頭獲利。
華爾街有句老話:“給人一條魚,你可以養活他一天;教會他如何套利,你就能養活他一輩子。”
我要在這裏做個記號,爲自己的“兩眼論”(來自圍棋的類比)增加一些例證:
1、索普在21點遊戲中戰勝賭場的兩個眼是“大數定律”和“凱利公式”;
2、格裏芬的可轉債套利,則是利用兩個“眼”之間的對衝。
格裏芬18歲開始建立了自己的可轉債套利組合。22歲那年,他用420萬美元建立了自己的基金公司--Citadel。
某種意義上,格裏芬繼承了索普和香農的衣鉢,他運用數學、計算機和金融智慧,再加上華爾街的慾望,和鯊魚般的兇狠,以及企業家的野心,開創了自己的金錢帝國。
2
格裏芬的Citadel有兩塊兒生意:
一個淘金,一個賣水。——也算是“兩眼”。
一、淘金的是Citadel對衝基金,其資金規模約爲530億美金,可能是有史以來最賺錢的對衝基金。
在過去32年裏,Citadel爲投資者帶來了近20%的平均年收益率,僅兩年出現過下跌。當然,有一年跌得很慘。
二、賣水的是Citadel證券,是世界上最大的做市商之一,也是美國最大的期權做市商,執行了美國上市股票期權量的約25%。
Citadel證券的盈利來自“麪包屑”,也就是買賣價之間的價差。
麪包屑雖小,但總量驚人。利用強大的計算機力量,看不見的“幾美分”價差,在自動化與流量的魔法之下,匯聚成河。
Citadel證券在2022年創造了75億美元的收入。
2021年的美國散戶大戰中,散戶們抱團“打爆空頭”,零傭金的Robinhood成爲交易主戰場。
賣水的Citadel證券,利用一種有爭議的“訂單流支付”的方法,執行了Robinhood的大部分交易。
差點兒被散戶們打爆的空頭Melvin Capital,後來得到了Citadel對衝基金約20億美元的投資。
左手淘金,右手賣水。
作爲最早的寬客之一,格裏芬沒有試圖讓自己成爲股神,而是將公司打造爲一家平臺型的賺錢機器。
不是成爲更厲害的賭徒,而是成爲賭場;
不是去當“更快的槍手”,而是成爲“更快槍手”的搖籃和樂土。
3
概括而言,格裏芬的Citadel採用了多元化的投資策略,以及多個投資組合經理的賽馬機制。
作爲多策略對衝基金,Citadel涵蓋了股票、全球固收和宏觀、大宗商品、信貸,以及量化等策略。
在這個愈發充滿了不確定性的世界裏,尤其是在疫情這幾年,多元化策略看起來更能應對波動,對衝風險。
相比較而言,單一策略顯得單薄了。
例如,2022年老虎環球虧損達54%。
被稱爲“小虎隊”的幾隻大名鼎鼎的對衝基金,由於類似的投資策略,例如大量買入成長股,也一樣遭遇了困境。
分散和賽馬的人才機制,似乎也有利於分散風險。
Citadel運營模式爲多經理平臺制度:
1、公司擁有衆多投資組合經理,各自招募數個研究員組成一個小團隊,管理公司的一部分資金;
2、每個團隊獨立運作,按照收益等指標優勝劣汰;
3、Citadel作爲大平臺,爲團隊提供後臺支持。這有點兒像美國特種部隊模式。
顯然,這種模式離不開強大的後臺系統和技術支持,還需要獨特的企業文化。
這與同樣有量化背景的對衝基金千禧年頗爲類似:
“千禧年採用MOM平臺的管理架構,即尋找最優秀的基金經理,組成團隊,分配資金。不限制個人投資風格,一切以業績說話。底層資源共享,發揮平臺力量。”
2021年千禧年有超過270個“槍手”,半年考覈一次,淘汰率極高。同時也會迅速補充新的“槍手”。
格裏芬曾經談及自己對人才和技術的態度,他認爲:
平衡“新技術的浪潮”和“人類思維的力量”,對於金融市場內外更好的決策至關重要。
簡單來說,就是“人機結合”。
如果說亞馬遜或者美團是將技術平臺與終端勞動力結合,那麼Citadel則是試圖將技術平臺與決策人才結合。
我在哈佛大學的網站上,看到這樣一段文字:
“Citadel渴望獲得的競爭優勢,來自能夠使用技術、機器學習和人力資本來積累所有可用的公共數據,然後“提取最相關的信息,然後能夠對這些數據進行正確的解釋。”
Citadel以多種方式使用機器學習,主要用於幫助預測同一商店銷售額等指標,識別投資組合中的風險,併產生想法。
然而,Citadel的機器學習被用來幫助人類判斷,而不是取代它。”
此外,公司會運用技術和金融手段,讓投資組合經理在設定和監控的風險限度內,實現自己與“賭神”對賭的稍縱即逝的天才想法。
4
格裏芬的基金公司早年被稱爲金融領域的谷歌,後來人們又說他是金融領域的馬斯克。
的確,與佩奇和馬斯克一樣,格裏芬也是運用技術和人才來重新塑造自己所在的領域。
這裏面,沒有比匯聚一幫絕頂聰明的專業人士更重要的事情了。
有兩個讓人印象深刻的故事。
故事一:2020年疫情初期,Citadel證券把1000多臺服務器和一部分交易員從紐約和芝加哥搬到了佛羅裏達棕櫚海灘的四季酒店。
當全國禁閉時,格裏芬的50名核心員工每天在四季酒店辦公。
故事二:2022年12月,格裏芬還自掏腰包請了大約1萬名員工和他們的家人聚集在佛羅裏達州的迪士尼樂園,在魔法王國和其他主題公園舉行了爲期三天的慶祝活動。
在Citadel官網首頁,羅列着公司各種奧林匹克競賽獎牌得主、各種博士、各種工程師、各種金融人士和量化人才等等,並宣稱:
我們彙集了聰明的頭腦,做別人認爲不可能的事情。
高盛前首席執行官勞埃德·布蘭克費恩曾經這樣誇自己的朋友格裏芬:
“他是一個偉大的交易員,但他也是一個偉大的商人,而這些東西通常不會同時出現。這就像一個在 100 米短跑和馬拉鬆比賽中都獲勝的跑步者。”
通常,交易員如孤狼,需要冷酷殘暴;而商人需要聚合資源,聚合人。
做投資的人總是希望長期戰勝市場。
要實現這一點,就像是和地心引力對抗。
一個人無法靠扯自己的頭髮離開地球表面,但是機器可以。
企業之作爲機器,亦是對抗“熵增”,對抗“市場有效理論”,對抗生命週期,對抗財神的隨機性支配。
而在這個機器裏,最重要的,依然是宇宙間最神祕的東西之一:
人類的大腦。
5
愛因斯坦可能沒有想過,自己關於布朗運動的研究,會與金錢如此緊密關聯。
比他更早5年,孤寂的路易斯·巴舍利耶於1900年,從隨機過程角度研究了布朗運動以及股價變化的隨機性,並提出了其後數十年世人都無法理解的觀念:
過去、現在的事件,甚至將來事件的貼現值反映在市場價格中。
股價遵循公平遊戲(fair game)模型。
1956年,物理學家奧斯本將巴舍利耶的布朗運動模型改進爲幾何布朗運動模型。
1964年,法瑪使用隨機遊走模型描述股票價格變化,提出了著名的有效市場假說。
1965年,薩繆爾森給幾何布朗運動模型增加了線性漂移項,建立了帶漂移的幾何布朗運動模型,從而解釋了股價的長期線性趨勢。
1970年,布萊克和斯科爾斯推導出了著名的B-S期權定價公式,利用數學工具解決了股票、債券、貨幣、商品等金融衍生產品的合理定價問題。
大約是在同期,索普幾乎使用了類似的方法,計算出期權價值,以實現股票和期權之間的套利。
1990年,格裏芬剛上路時,索普將自己過去的一些可轉換債券和權證的招募說明書送給他,這位年輕人由此幸運地不必從頭探索金礦之所在。
聰明的交易者們一邊將B-S期權定價公式當作基本的工具,一邊千方百計讓自己成爲與“有效市場假說”相愛相殺的鯊魚:
鯊魚們通過獵殺肥美的食物,讓市場變得有效。
這似乎也是套利:在有效和即將有效之間套利。
“有效市場理論在4/5的時候都是成立的,投資者可以利用剩下1/5的機會。”
B-S期權定價公式像是牛頓的定律。有效市場假說像是“地心引力”,將所有試圖用自己的聰明才智在市場上絞殺不如自己聰明的傢夥的天才們拖回地面。
即使是最讓“有效市場假說”理論頭疼的巴菲特,雖然自己連續多年擊敗標普500,也不止一次嘲諷了研究公式與理論的教授,卻也站在“跑贏指數很難”這一側。
巴菲特打過一個世紀之賭,他在2007年買入先鋒的S&P 500指數型基金,對手則精選了5只對衝基金。
巴菲特的“賽馬”第一年(2008)就虧了37%,對手虧了23.9%。
十年後,巴菲特仍然贏了。“無聊的指數”再次跑贏專業人士精心挑選的、由頂尖聰明人操作的對衝基金。
一個理性的人會捍衛自己的觀點,但也不拒絕在相反的方向下注,以實現對衝。
就像堅信“市場有效”的薩繆爾森,也買入了“與自己理論不符”的巴菲特公司的股票。
最後
雖然格裏芬也會和巴菲特一樣,在自己的大型獵物出現困難時出手。但是,他似乎不關心股票的基本面或內在價值,只關心價格波動。
的確,從一開始,他就和索普一樣,通過套利來賺錢,而不是去做“更快的槍手”。
經濟學家羅伯特·席勒在《非理性繁榮》一書中指出:
“我們應當牢記,股市定價並未形成一門完美的科學”。
和愛因斯坦研究的布朗運動的隨機遊走不一樣,人類的金錢世界交織了太多複雜元素。
鐘形曲線無法涵蓋所有不確定要素,慾望,槓桿,羊羣效應,肥尾,令黑天鵝事件頻頻發生,給人們以致命打擊。
塔勒布認爲“數理金融學理論的有效性與佔星術一樣不靠譜”,並指責數理金融學“一直使金融體系面臨崩潰的風險”。
格裏芬的Citadel也曾經在2008年遭遇大幅虧損,他後來反思:
困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過於自負,即相信自己有能力安度任何市場災難。
慾望永遠不會止步,人們總是忍不住與“財神”對賭,哪怕隨機性像是上帝的嘲諷和戲弄。
爲了實現超額回報,聰明人們使用各種方法加上槓杆:
賭徒們喜歡無限制地加資金槓桿;
價值投資者們則是加長期的時間槓桿;
量化交易者們加高頻的槓桿。
格裏芬降低了早年的資金槓桿。他一方面加大了科技槓桿,一面通過組織創新和人才戰略,實現了分佈式的聰明大腦槓桿,讓自己的套利遊戲越玩兒越大。
他已經走了很遠,未來還能走多久?
假如巴菲特仍然有時間與格裏芬打一個十年之賭,誰會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