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後,面對小金人,賈登·史密斯將會想起父親在奧斯卡典禮上毆打頒獎嘉賓的那個遙遠的夜晚。
換種説法,假如多年以後仍然有人記得今年這場奧斯卡頒獎典禮,那麼除了這記響亮的耳光之外,其他值得一提的亮點實在不多。
除了克里斯洛克的半邊臉,今晚洛杉磯杜比劇院在場的所有人都要感謝威爾·史密斯,他用右手拯救了這屆無聊的奧斯卡。
但越來越窘迫的奧斯卡,與山河日下的好萊塢電影,又要靠誰來拯救?

01
電影背離藝術
如果要用一句話形容第94屆奧斯卡,應當是“拳頭與眼淚並行,政治共藝術一色”。
威爾·史密斯扇耳光的手兀自痠麻,眼角淚水未乾,這邊最佳男主角頒獎嘉賓已經念出他的名字,可謂是“温淚拿影帝”。
另一位大贏家是華納,製作發行的《沙丘》斬獲6項大獎,分別是最佳攝影、最佳視覺效果獎、最佳原創配樂、最佳音效、最佳剪輯和最佳藝術指導——全部為技術獎項。尷尬的是,統籌一切的丹尼斯·維倫紐瓦卻未獲得最佳導演提名。

維倫紐瓦之前執導的《銀翼殺手2049》與《降臨》都因豐富的視聽表現力受到廣泛稱讚,因此被業界和影迷們認為是最適合《沙丘》的人選。後者卻未能複製他在科幻題材的成功,1.65億美元的製作成本只換來3.5億美元全球票房,算是血虧。
科幻史詩終究敗給了西部風情,《犬之力》拿下12項提名,簡·坎皮恩最終力壓斯皮爾伯格、保羅·托馬斯·安德森與濱口龍介等一眾名導拿下小金人,再次為女性導演做出表率。
近兩年,女性在奧斯卡的地位愈加重要。去年趙婷和她的《無主之地》大出風頭,今年則輪到了簡·坎皮恩和夏安·海德,後者執導的《健聽女孩》獲得最佳影片和最佳改編劇本兩項大獎,頗出業界意料之外。
再加上朱利亞·迪庫諾憑藉《鈦》拿到戛納電影節金棕櫚獎,奧黛麗·迪萬憑藉《正發生》拿到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和卡拉·西蒙·皮坡憑藉《阿爾卡拉斯》拿到柏林電影節金熊獎。
那麼在一年之內,世界三大電影節和奧斯卡同時把獎項頒給了女性導演。

相比最佳導演和最佳影片,最佳國際影片頒給《駕駛我的車》幾乎是最沒有爭議的結果。該片在奧斯卡之前已在全球各地斬獲17座年度最佳影片獎。
濱口龍介平緩細膩的敍事手段與村上春樹原作小説在韻律上達成完美共振,此前被認為有望在《寄生蟲》之後,為亞洲電影拿下第二部非英語的奧斯卡最佳影片。
非英語地區的崛起也是奧斯卡不容忽視的浪潮。
單從近幾年來講,亞洲這邊有韓裔導演李滄東、奉俊昊和李·以薩克·鄭,和日本的是枝裕和、濱口龍介,南美則有墨西哥三傑——阿方索·卡隆、吉爾莫·德爾·託羅和亞利桑德羅·岡薩雷斯·伊納裏多。在2013年以來的9年裏,亞裔和南美裔導演拿走了7座最佳導演獎。
奧斯卡的政治正確在題材上體現得最明顯。
今年最受關注的《犬之力》仍然講述同性戀愛故事,雖然換了一種內斂和曖昧的手法,仍然是從《月光男孩》到《以你的名字呼喚我》在內容上的延續。
幫史皇拿下又一座影帝獎盃的《國王理查德》則屬於黑人題材,和前幾年的《黑豹》、《綠皮書》、《逃出絕命鎮》一樣在輿論上大獲成功。
今年的奧斯卡創造了新的歷史,即監製團隊全部由黑人組成。再加上三位主持人身上體現出來的黑人、女性、大碼潮流等許多元素,多元化發展趨勢已經不能再明顯。

蕾吉娜霍爾、艾米舒默和汪妲賽克絲(從左至右)
並且在制度保證下,這種趨勢今後會越來越明顯。
從2024年開始,從影片主題、劇組人員構成到製片公司員工,都必須包含一定比例的少數族裔、女性、跨性別者或身障者,才有資格角逐奧斯卡。
從最開始以《亂世佳人》為代表的都市愛情,到後來用《阿甘正傳》孜孜不倦地宣揚美國精神,再到如今所謂的政治正確,奧斯卡在每個時代都不吝於從普世價值角度傳遞觀念與取向。
當然,這並不是奧斯卡收視率連續打破新低,在2014年到2021年內從4370萬下降至985萬的最主要原因。
02
特效難敵流量
在一以貫之的政治正確和分豬肉之外,今年奧斯卡仍然延續了另一個無法忽視的趨勢——流媒體的崛起。
比如分別斬獲最高獎項的《健聽女孩》與《犬之力》,分別是Apple TV+和Netflix兩大流媒體今年重磅推出的衝奧之作。前者成為歷史首部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的流媒體原創電影。
同樣由Netflix製作發行的《不要抬頭》與《犬之力》一同落敗,《不要抬頭》獲得4項提名,最終卻連最有把握的最佳原創劇本獎都撼負《甘草比薩》。Apple TV+出品的《麥克白》與其同病相憐,同樣3提0中。
《國王理查德》和《沙丘》在獎項上各有收穫,如果這兩部電影因為遵照華納在院線與流媒體HBO Max同時上映的發行策略,只能勉強算作“流媒體電影”。
那麼,扎克·施奈德直接在流媒體發佈的《活死人軍團》和《扎克·施奈德版正義聯盟》則與院線電影涇渭分明。這兩部電影分別獲得粉絲票選最愛電影和粉絲票選歡呼時刻兩個獎項。

與流媒體的春風得意相比,傳統院線電影顯得更加落寞。
老牌名導斯皮爾伯格和雷德利·斯科特的《西區故事》、《古馳家族》與《最後的決鬥》三部電影都在票房、獎項上雙雙滑鐵盧。中生代導演們帶來的《貝爾法斯特》、《甘草比薩》與《法蘭西特派》也未能扛起院線的榮耀。
質變來源於量變,Netflix近三年在奧斯卡屢屢得手,是因為獲得提名分別為24、35和27項,連續壓倒各大製片廠。之所以能有這麼多提名,又是因為有海量電影可供大浪淘沙。
2021年,Netflix在內容製作上的投入高達170億美元,全年推出70多部電影,意味着用户每週都能在Netflix看到新上線的電影。
作為對比,好萊塢傳統制片廠中的老大迪士尼,2021年在內容製作上的投入只有20億美元,計劃推出的電影數量也只有23部。
流媒體之所以能對傳統制片廠形成降維打擊,主要原因是商業模式不同。
電影從誕生之日起就天生帶有兩項致命的弱點。第一,投資高、週期長,並且無法預測收益。因此好萊塢雖然憑藉視效大片征服全世界,各大製片廠卻一直在走鋼絲。
比如米高梅,投入1.15億美元重金押注吳宇森的《風語者》,最終分賬票房不到3000萬美元。從此一敗塗地,昔日的好萊塢之王落得個賣身還債的結局。
另外一個弱點是依賴院線,疫情之下這一點更加明顯。從2020年到2021年,北美年度電影票房分別只有22.8億美元和45.5億美元,便是受疫情影響影院無法正常營業所致。

Netflix卻能在2020年和2021年分別實現250億美元和297億美元營收,就是因為完美擺脱了傳統制片廠這兩項弱點。
首先,流媒體重新掌握製作、發行到放映端完整產業鏈,因此不用向院線支付昂貴分成;其次,流媒體做的是流量生意。只要用户增長就旱澇保收,電影質量成了次要因素。
總而言之,流媒體掌握了更為先進的商業模式,傳統制片廠要想不被消滅,只能改變自己。所以我們看到傳統獨立製片廠紛紛依附於大型媒體集團,而後逐漸成為流媒體的附庸。
迪士尼是其中的典型代表,2019年11月推出流媒體服務,一年半之後訂閲用户總數便突破1.7億,幾乎與Netflix分庭抗禮。迪士尼當然還沒放棄院線,但流媒體的錢如此好賺,資本家畢竟和藝術家不同,他們又能堅持多久呢。
20世紀40年代時,好萊塢八大製片廠壟斷了全美17%的電影院,獨立電影人和院線淪為壟斷製片廠的附庸。
大製片廠製作的電影再垃圾,觀眾們也別無選擇,好在一紙《派拉蒙法案》終結了電影托拉斯。
如今流媒體再次有一統江山的趨勢,傳統制片廠在疫情之下本就是掙扎求生,又能指望它們拍出多少好電影。目前Netflix正與迪士尼+等爭奪市場,還需要從質量上分高下。
然而等這一場戰爭塵埃落定,勢必形成新的壟斷。如果將來流媒體也給觀眾喂屎,還會有另一張法案,來拯救這個市場嗎?
至於那時的奧斯卡,註定一代不如一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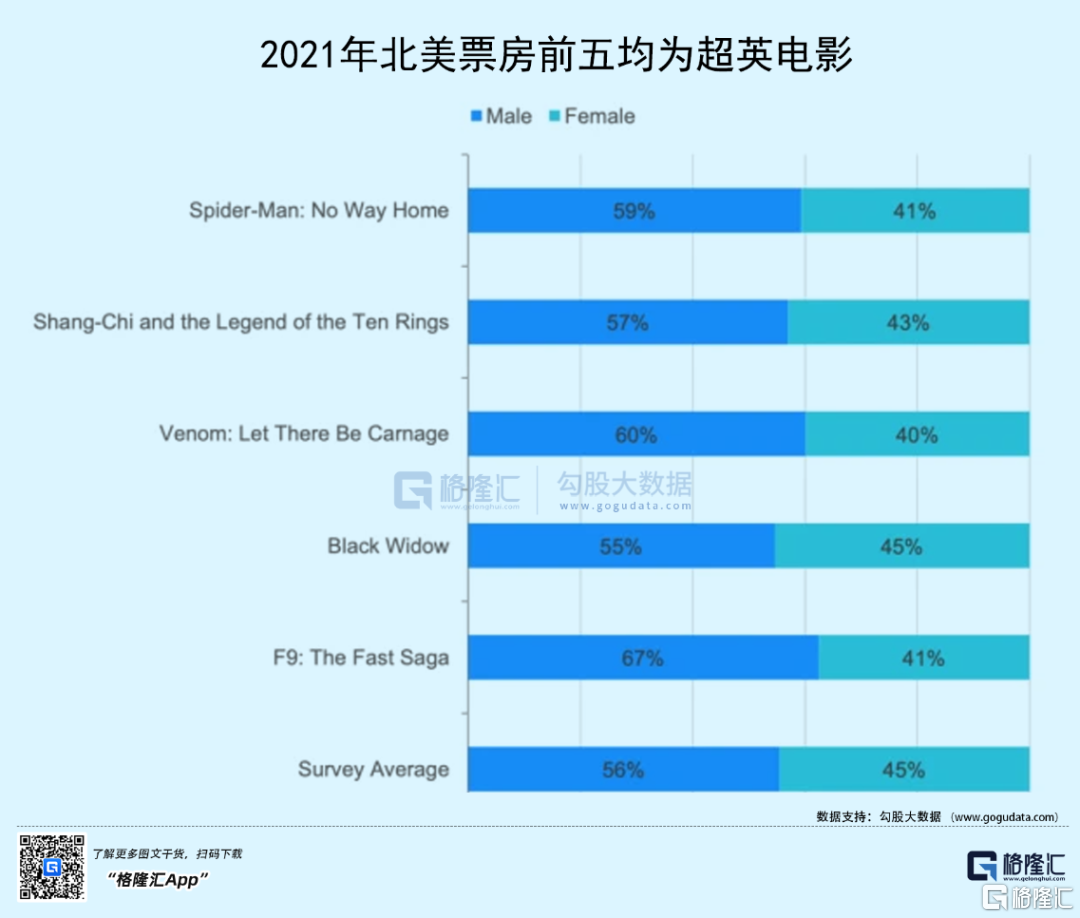
03
結語
奧斯卡的創辦者是路易斯·梅耶,他也是米高梅的創始人之一,為好萊塢留下了“為藝術而藝術”的座右銘,然而如今連米高梅都已賣身亞馬遜。
在今天的奧斯卡開始之前,兩屆“影帝”西恩·潘公開用“熔燬小金人”威脅主辦方請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頒獎典禮上發言。
所謂“讓藝術迴歸藝術”或“藝術無關政治”,在21世紀的今天,已成空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