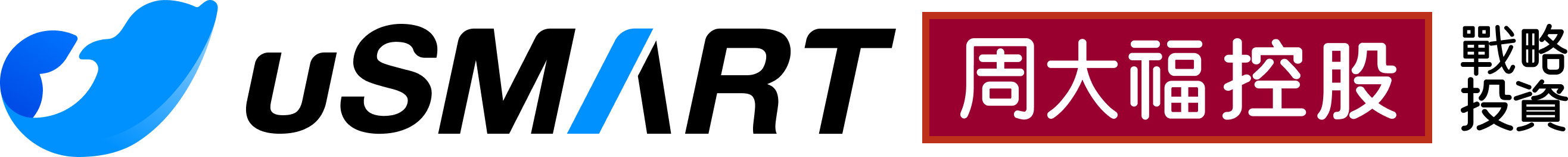本文來自格隆匯專欄:鄧海清,作者:鄧海清 汪術勤
當地時間21日,俄羅斯總統普京簽署承認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和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的總統令,並簽署俄羅斯與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和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的友好合作互助條約。俄羅斯《觀點報》22日報道稱,網上有消息稱俄軍已開始抵達頓巴斯地區。
近期俄烏緊張局勢引發各界廣泛關注,美國在東歐地區頻頻“挑事”。在當前全球大國博弈背景下,美國在烏克蘭的“小動作”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矛頭直指德法,意在削弱、肢解歐盟,阻止法、德、俄因能源聯繫(北溪二號)進一步聯合,阻撓歐洲真正實現一體化。
俄烏緊張局勢進一步升級,美國、英國、俄羅斯各有所得,最受傷的除了烏克蘭,就是歐盟,尤其是德法。歐盟一體化危機進一步加劇,未來3—5年全球最大的灰犀牛不是中國或俄羅斯,而是歐盟的衰落或分裂。
一、美日貿易戰,歐盟趁勢崛起:廣場協議後的日本“窮途末路”VS德國“涅槃重生”
1985年,美國聯合西方主要經濟大國,迫使日本簽署著名的《廣場協議》,日元匯率大幅升值,從1985年到1987年日元對美元升值超過50%,極大地削弱了日本出口產業的國際競爭力,造成產業鏈向海外轉移。
面對美日貿易戰,日本政府的危機應對出現失誤。日本政府選擇了對外升值(日元升值)、對內貶值(貨幣寬鬆)。出口受到影響後,為了維持經濟增速,日本政府通過貨幣放水和財政擴張進行刺激,但忽視了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這一根本性措施,結果治標不治本,大量資金湧入房地產市場和股市,催生資產泡沫,並對技術創新投資形成抑制。疊加當時日本人口老齡化加速,經濟活力下降,最終泡沫破滅,日本經濟長期低迷。
但《廣場協議》並非單獨針對日本,在《廣場協議》中,聯邦德國作為貿易順差國,也被同樣要求貨幣對美元升值。日德兩國貨幣在1985-1987年間經歷了幅度接近的升值,但兩國在資產價格及後續長期增長上表現卻大為迥異。
德國能夠順利“軟着陸”,一是因為德國央行在二戰後一直旗幟鮮明地反對高通脹,對貨幣寬鬆的態度非常審慎,這種態度甚至一直影響到歐央行的貨幣政策目標。廣場協議導致德國經濟增速下降,德國央行下調存款利率穩增長,但同時提高了存款準備金率防止流動性的泛濫。
二是因為德國外貿出口對美國的依賴程度更低,對歐洲其他國家出口佔比較高。同時歐共體於1972年達成了匯率聯動機制,區域內各國貨幣間的波動幅度限定在2.25%以內,因此雖然德國馬克兑美元匯率快速升值,但對其他主要出口對象的匯率比價依然保持相對穩定。
三是因為德國沒有刺激房地產和資本市場,而是注重於經濟結構轉型升級,提高製造業的競爭力和技術水平。日本在廣場協議後的財政政策擴張偏重於大搞基建,而德國財政政策主要是對企業和個人大幅減税,通過財政補貼支持企業的研發投入,資助一些利潤低、投資週期長、風險大的生產行業等等,保證了資本“脱虛向實”,德國實體經濟競爭力並未受到損害。
20世紀90年代之後,日本在美日貿易戰衝擊之下進入所謂“失去的20年”,經濟陷入衰退和超低速增長;蘇聯解體,東歐劇變,歐盟的外部壓力極大減輕,整個西歐一片欣欣向榮。在此背景下,歐洲趁勢崛起,1993年歐盟成立,1999年歐元投入使用,歐洲一體化進程大步邁進。
二、歐元信任危機:貨幣大放水動搖歐央行“立行之本”,侵蝕歐元信用基礎
(一)第一次歐元信任危機:北約轟炸南斯拉夫聯盟
1999年歐元投入使用,外界一度認為歐元將取代美元成為21世紀的世界貨幣。但很快歐元就遭遇了第一次信任危機。美元霸權是建立在美國的政治、經濟、軍事、科技霸權的基礎之上的。1999年美國主導的北約轟炸南斯拉夫聯盟,再次展示了美國的軍事和政治霸權。大家發現歐元的信用基礎並不牢固,歐盟實際上無法主導歐洲事務,引發歐元匯率貶值。
(二)第二次歐元信任危機:歐洲主權債務危機與歐央行“負利率+QE”大放水
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經濟遭受重創,暴露出金融市場“有毒資產”(房地產次級貸款及其衍生品)的重大缺陷,歐元再一次迎來“逆襲”的機遇。但2010年希臘主權債務危機突然爆發,並向葡萄牙、愛爾蘭、意大利、西班牙等歐洲其他國家擴散,形成歐債危機,外界發現歐元區的“有毒資產”(歐元區中較弱的經濟體的主權債務)危害並不比美國弱。
同時,為了避免危機傳導,歐盟推出了一項總額7500億歐元的救助機制,並通過歐央行購買這些國家的國債,歐盟和歐央行引以為傲的財政紀律和貨幣紀律遭受廣泛質疑,歐元持續貶值,引發外界對歐元的第二次信任危機。
(三)第三次歐元信任危機:“滯脹”形勢下歐央行進退兩難
2020年新冠疫情後,歐美央行紛紛開啟QE閘門,實行以貨幣政策超級寬鬆配合財政政策向居民發放現金的“財政赤字貨幣化”政策,這一政策帶來貨幣濫發,通脹高企,嚴重侵蝕了貨幣的信用基礎。為抑制高通脹,2022年美聯儲即將開啟加息縮表進程,但歐央行面臨的形勢則更加複雜嚴峻:
美聯儲加息是建立在經濟和就業數據大幅好轉的基礎之上的,但歐元區則面臨着類似於“滯脹”的形勢。
一方面,歐元區的核心通脹創出歷史新高,能源價格飆漲。與美國能源可以實現自給不同的是,西歐能源嚴重依賴進口,因此高通脹對西歐國家的打擊更大。且歐央行從貨幣政策目標上看更加傾向於抑制通脹,加息似乎刻不容緩。
另一方面,西歐國家疫情防控較為失敗,產業鏈和供應鏈的恢復緩慢,經濟恢復程度遠不及美國。
同時,歐元區不是美國這種統一的國家,國家間協調的成本和難度更高,尤其對於當前經濟增長較疲弱、債務壓力較大的成員國來説,更不願意看到貨幣緊縮。
因此,當前歐央行面臨兩難選擇:加息則可能導致經濟和就業狀況進一步惡化,債務違約風險上升,民怨沸騰,成員國離心力增強;繼續寬鬆則可能導致高通脹長期化,並繼續侵蝕歐元的信用基礎。
歐元作為一種統一貨幣推出,其初衷是為了加強歐盟內部的團結,但從結果來看可能加劇歐盟的分裂。
三、歐盟戰略自主雄心與美國戰略的衝突:一個團結的歐盟不符合美國霸權利益
在當前大國博弈中,歐盟處境堪憂。一方面,歐元區經濟總量增長緩慢,與中美差距加大。從2010年至2020年的10年間,中國實際GDP年平均增速為6.82%,美國為1.62%,歐元區僅為0.51%。在互聯網、數字經濟、航空航天、芯片等領域,歐洲進展也明顯落後於中美。另一方面,美國為拯救其日益衰落的霸權,希望將歐盟肢解、綁上戰車,並推動中歐脱鈎,這意味着歐盟將損失中國市場,淪為淨輸家。
當前俄烏局勢緊張,對歐盟形成雙重衝擊:一是持續的危機推升了能源價格,加劇了西歐通脹形勢;二是危機再次彰顯了歐盟的短板,即政治上和軍事上受制於美國。
從美國的利益出發,局部衝突激化甚至交火對美國實則有利:(1)促使東歐國家由於不安全感而向美國靠攏,尋求美國軍事政治庇護,歐盟無法實現戰略自主,被迫加入美國陣營與中俄對抗,德法也將喪失對歐洲事務的話語權和自主權;
(2)進一步加劇西歐能源供應緊張局勢,推升其通脹,打擊歐洲經濟;
(3)推動全球資本出於避險目的迴流美國,推升美元指數,拯救美元霸權。
當前歐洲也在積極自救,比如出台芯片法案和數字税法案,爭奪數字時代制高點;在俄烏之間積極斡旋,緩和緊張局勢。但歐盟對美國科技霸權和政治霸權的挑戰也更加堅定了美國進一步“肢解”不聽話的歐盟的決心。美國科技霸權需要龐大的市場支撐,一旦失去了中國、獨聯體和東南亞市場,要想支撐美國科技企業的營收增長,必須保住歐洲市場。
遺憾的是,當前歐洲政壇上缺少具有廣泛國際影響力的資深政治家,在民粹主義思潮影響下通過選舉上台的年輕領導人缺乏足夠的政治歷練和政治資源,難以左右歐洲局勢,緊急斡旋往往收效甚微。
2016年6月,英國全民公投決定“脱歐”,為歐盟其他成員國做出了一個壞的示範。脱歐之後,英國財政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增強,並向美國靠攏。2021年12月,英國央行率先打響美日歐央行新冠疫情以來加息的“第一槍”,將基準利率上調15個基點至0.25%;2022年2月份,英國央行再次將基準利率上調25個基點至0.50%。
東歐局勢緊張,歐元區和歐盟危機加劇,歐洲資本可能將英國倫敦作為避風港,從而利好英國金融業和地產業。如果未來英國央行在控制通脹和促進就業方面表現優於歐央行,可能進一步刺激其他歐盟國家考慮“脱歐”。
從歷史上看,只有在美國霸權極其強大時,才會給予歐洲較大的戰略自主空間;而當美國霸權衰落或面臨較大外部威脅時,就會加強對歐洲的控制,使之成為美國爭霸的“馬前卒”:
二戰結束後法國“戴高樂主義”宣揚歐洲戰略自主,但美國需要藉助西歐的力量與蘇聯進行冷戰。最終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加強對西歐的控制,建立北約,構築“鐵幕”,西歐不得不登上美國的戰車,“戴高樂主義”不了了之。
到了90年代,蘇東劇變,日本陷入“失落的二十年”,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經濟上進入“新經濟”繁榮,海灣戰爭彰顯軍事霸權,戰略上極度自信,才給予了歐盟崛起的機會,90年代是歐洲一體化快速推進的黃金時期。
進入21世紀後,美國再度加強對歐盟的控制,無論是布什政府推出的“新老歐洲”區別對待以打擊不聽話的德法(德法反對布什政府發動的伊拉克戰爭),還是近年來美國逼迫歐盟站隊,以及對歐元的打壓,都表明美國為維護霸權意在重新加強對歐洲的控制。
美歐在俄烏衝突中的不同表現折射出歐盟戰略自主雄心與美國霸權戰略的衝突:在美國霸權衰落的階段,為更好地控制歐洲,必然要打壓歐盟戰略自主,阻止德法俄的聯合,加大歐盟分裂,使歐盟唯美國馬首是瞻。
昔日美日貿易戰和美蘇冷戰的結果是日本衰落、蘇東劇變,歐盟趁勢崛起;當前中美博弈的結果很可能是歐盟衰落或解體,中國“一帶一路”崛起。未來3—5年全球最大的灰犀牛不是中國或俄羅斯,而是歐盟衰落或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