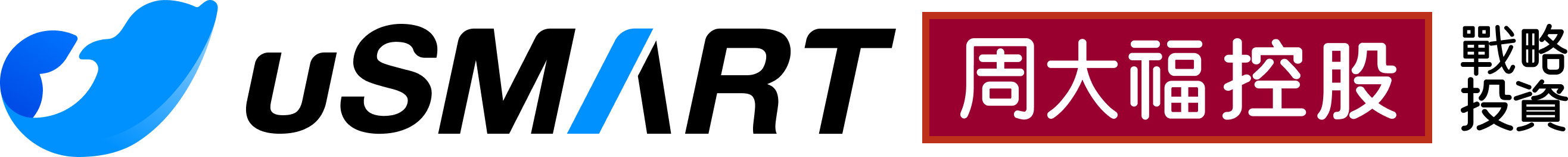本文來自格隆匯專欄: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作者:徐奇淵 楊子榮
摘要
☞ 當前中美利差顯著收窄,二者的舒適區間很可能已經明顯低於80個基點的水平,人民幣匯率對利差的敏感度在下降。從利差角度來看,中國的貨幣政策空間正在變大。即便在貨幣政策寬鬆的過程中,人民幣匯率在一定程度上走弱,這也不應當影響到宏觀政策“以我為主”的基調。在此背景下,中美利差收窄不應成為我國貨幣政策寬鬆的障礙。
☞ 中美利差收窄的同時,人民幣匯率卻持續走強。這種偏離的主要原因是中美金融市場風險的相對形勢發生了變化。
☞ 當前,美國通脹壓力持續上升、聯儲對市場預期的引導失敗,同時增長動能漸弱。在此背景下,美聯儲迫於形勢,不惜可能的代價而推出“壞”的加息。這也進一步增加了美國金融市場的風險。美聯儲的政策平衡術正走在一條十分狹窄的獨木橋上。
☞ 中國已經實施和將要實施的寬鬆政策是“好”的寬鬆,有助於降低市場風險、增強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期、穩定投資者信心。
——徐奇淵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特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楊子榮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
中美利差收窄無礙貨幣寬鬆
中美利差顯著收窄,但人民幣匯率沒有遵循利率平價出現貶值。這種偏離的主要原因是中美金融市場風險的相對形勢發生了變化。受此支撐,中國貨幣政策的空間仍然較大。
2022年初以來,美國通脹壓力持續超預期,美聯儲寬鬆貨幣政策退出、加息進程陡然提速,同時中國不斷釋放穩增長的政策信號。
在此背景下,中美10年期國債利差已經從2021年最後一個交易日的125個基點,迅速縮小到了2022年2月18日的88個基點。甚至在2月10日,利差一度收縮到了70個基點。
中美利差已經降到了歷史低位,稍高於2015年以來的幾個歷史低點。再結合利差的下行方向,當前情況與2015年12月中旬、2016年11月初、2018年8月中旬等時期相似。
而在這幾個時間段,中國都曾經面臨資本外流、匯率貶值的較大壓力。這也引發了擔憂:中美利差降至低位,是否會出現資本外流風險,是否會成為貨幣政策寬鬆的掣肘?
 數據來源:WIND金融終端,作者計算。
數據來源:WIND金融終端,作者計算。
風險因素是理解當前匯率走勢的重要角度
當前,中美利差縮小至歷史低位,但人民幣匯率卻持續走強,屢創2018年以來的新高。如何理解人民幣匯率對利率平價的偏離,這種偏離是否可持續?
對於這種偏離的回答,一般的解釋因素有:資本管制、外匯市場干預、風險因素。
近年來,人民幣匯率的彈性顯著上升,沒有證據表明外匯市場干預對匯率產生了影響。同時,自2018年以來金融開放明顯擴大,跨境資本流動的便利性也在上升。
事實上,前兩個因素都有助於匯率向利率平價趨近。因此,要理解近期人民幣匯率對利率平價的偏離,只有從風險因素角度入手。
美國“壞”的加息,市場風險在上升
從美聯儲加息的角度來看,基於加息原因,可以將美聯儲的加息事件分為“好”的加息、“壞”的加息。
“好”的加息,是在就業改善、經濟持續增長背景下出台的加息政策。“好”的加息雖然也是緊縮政策,但是伴隨着基本面持續景氣,金融市場也會呈現出比較樂觀的走勢。例如美聯儲在2016年到2017年的操作就是“好”的加息。
而“壞”的加息,是在基本面差強人意的基礎上,迫於通脹上行壓力而被動推出的加息政策。“壞”的加息可能對美國金融市場本身產生一定負面衝擊。
與上一輪“好”的加息形成對比,這次美聯儲正在推動“壞”的加息。
2021年,美聯儲反覆強調通脹是“暫時的”,到後來改口認為通脹還將持續一段時間,美聯儲對市場預期的引導在一定程度上失敗了。
但是與此同時,美國的通脹率還在屢創新高,2022年2月CPI同比增速高達7.5%,創40年新高。其他關鍵指標,如核心PCE通脹率、以及經過剔除異常值處理的PCE通脹率都創下了歷史新高。
當前,推升美國通脹的因素中,供應鏈、能源的因素有所緩解,但是食品、工資、租金的推動作用在上升。
“壞”的加息的另一個重要背景,是美國增速預期的顯著下調。
2022年1月的最新預測中,IMF將美國2022年增速下調至4%,較2021年10月的5.2%大幅下調了1.2個百分點,在所有發達經濟體中的調降幅度最大。IMF調整的原因是,美國推出的“重建美好未來”財政刺激法案難產、美國提前退出貨幣寬鬆政策以及持續的供應鏈中斷。
同時,國際投行也紛紛下調2022年美國增速預期,當前市場預測均值為3.8%。高盛甚至將預測值下調到了3.2%,這也是去年7月以來,高盛第六次下調美國經濟增長預期。此外,從2022年一季度增速來看,根據亞特蘭大聯儲的GDPNow模型的最新預估,美國GDP環比折年率將降至0.1%,高盛的預測為0.5%。
市場主流觀點認為2022年美聯儲可能加息4次-6次,而截至2022年2月11日,美國10年期-2年期國債收益率利差僅剩0.42個百分點,這意味着市場預期美聯儲可能冒國債收益率曲線倒掛和經濟衰退的風險而持續加息以應對通脹壓力。
當前,美國通脹壓力持續上升、聯儲對市場預期的引導失敗,同時增長動能漸弱。在此背景下,美聯儲迫於形勢,不惜可能的代價而推出“壞”的加息。這進一步增加了美國金融市場的風險,截至2022年1月美股標普500席勒市盈率進一步上升至39.63,接近2000互聯網泡沫危機時的水平。美聯儲的政策平衡術正走在一條十分狹窄的獨木橋上。
中國“好”的寬鬆,市場的風險在下降
反觀中國,緊縮性的宏觀政策和金融監管政策大致在2021年9月達到頂峯,之後政策的一系列調整和糾偏使得國際投資者重拾信心。
尤其是2021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再次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強調2022年“經濟工作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各方面要積極推出有利於經濟穩定的政策,政策發力適當靠前”。
對於去年經濟工作中出現的合成謬誤和分解謬誤,經濟工作會議還重點強調了五個方面的“正確認識和把握”,對共同富裕、資本規範健康發展、碳達峯碳中和等問題的認識進行了糾偏,澄清了一些誤解。
今年初以來,中國宏觀政策靠前發力,新增信貸、社融均創新高,地方財政方面,專項債發行明顯前置。相比之下,2021年1、2月均無新增專項債發行,而今年以來(截至2月8日)已發行超過5000億元,完成提前下達新增專項債務限額(1.46萬億元)的35%。
按照當前進度,今年專項債的執行進度將大大快於去年。此外,房地產調控和監管政策也在邊際上有所放鬆。同時,一系列擴內需、穩外貿、保市場主體的政策也陸續出台。
中國已經實施和將要實施的寬鬆政策是“好”的寬鬆,有助於降低市場風險、增強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期、穩定投資者信心。中美風險反差,解釋了匯率對利率平價的偏離。
美國“壞”的加息和中國“好”的寬鬆,分別引致了美國市場的風險上升,中國市場的風險下降。這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中美利差縮小的同時,人民幣匯率穩定甚至持續走強,以及伴隨的資本流動方向。
我們分別觀察美國標普500波動率指數(VIX),以及美國市場上的中國ETF波動率指數(VXFXI),兩者分別用來描述美國、中國金融市場的風險。因為內地市場缺乏可比指標,所以我們使用了VXFXI。實際上使用香港市場的恆生波幅指數(VHSI)也有類似結論。
從月度均值來看,2021年9月VXFXI見頂,達到了32.5,在2022年2月的上旬則降至31.2,波動率指數降幅為4.1%。同期,美國的VIX指數從19.8上升到23.0,波動率指數上升了16.1%。可見這一時期,中國市場的風險逐漸有所緩解,而美國市場風險則有一定上升。
相應地,2021年9月之後,滬港通渠道的雙向資金淨流入總體上較為顯著,海外機構正在加速投資A股,包括在境外通過各種渠道投資中國市場的資產標的。
相反,2015、2016年正值美國處於“好”的加息時期,通脹壓力不大,就業、增長形勢較好,而同期中國則面臨較大金融風險壓力。
同樣觀察當時的中美波動率指數,2015年1至8月,中國ETF波動率指數(VXFXI)月均值從26.0上升到36.5,快速上升40%。同期美國的VIX指數從19.1上升到19.4,僅上升了2%。儘管2015年8月中美利差平均值高達130個基點,比2015年1月也只下降了37個基點,但是由於中美風險對比發生了重要變化,因此人民幣開始承受巨大壓力。可見在當時,風險因素也是解釋匯率的重要角度。
從國際收支角度來看,利率平價主要從跨境資本流動角度來解釋匯率變化。但是還要看到,經常賬户對於外匯市場供求關係也起到了重要作用。2021年上半年以來出口持續超預期,國際收支的大額順差對人民幣匯率形成了重要支撐。同時,涉外收入的結匯佔比也持續高於涉外支出的售匯佔比,這也反映了市場對人民幣匯率偏強的預期。
此外,從資本金融賬户本身來看,人民幣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作用在上升、中國債券市場被納入到MSCI等國際指數,這些中長期因素也在發揮作用,境外機構配置人民幣資產的需求上升,因此也支撐了一定的資金流入。
綜上所述,當前中美利差對於人民幣匯率的影響暫時居於次要地位,而非利差因素居於主導地位。
貿易順差方面,預計今年上半年仍將對外匯市場的供求維持一定的支撐。從風險因素來看,2021年9月之後中美市場的對比形勢發生了重要變化:美國方面,“壞”的加息導致市場風險上升;而在中國這邊,“好”的寬鬆將會進一步減少市場的風險,同時甚至可能對人民幣匯率起到穩定作用。
當前,中美利差的舒適區間很可能已經明顯低於80個基點的水平,從利差角度來看,中國的貨幣政策空間正在變大,人民幣匯率對利差的敏感度在下降。即便在貨幣政策寬鬆的過程中,人民幣匯率在一定程度上走弱,這也不應當影響到宏觀政策“以我為主”的基調。在此背景下,中美利差收窄不應成為我國貨幣政策寬鬆的障礙。包括貨幣政策在內的宏觀政策,有條件進一步向寬鬆方向進行更具實質性的調整,從而鞏固市場信心、推動形成積極的預期。